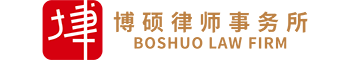妙文推荐:《为什么解释》
发布时间:2014-05-12 08:36:00 作者: 分享到:

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许多人生出“活在别处”的沧桑与无奈。也许,我们至今仍未走出唐德刚先生当年言说的“历史三峡”,被裹挟着向前,却又不知迈向何方。伤痕文学描摹的伤口还未结痂,一代人就迫不及待地“致终将逝去的青春”。一代人的惆怅远未散去,另一代人已开始在“小时代”里“拼爹”,直问“爸爸去哪儿”。对于法律,我们何尝不如是?法律好像就是一个我们嘲弄的对象,生来就是供我们发泄的。我们一方面高呼法治,好像一法治,我们马上就有钱,马上就有对象,马上就有一切;但另一方面,面对微观的法律,我们忽然就换了一副尊容,对规范吹毛求疵,好像不如此,就无法显示法律人的品位“高端大气上档次”。君不见,“某某法的缺陷及完善”铺天盖地,“某某法的反思与重构”遮云蔽日。我们能否稍安勿躁,解释那些看上去也许不那么美的法律?
一
2011年3月10日,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吴邦国先生自豪地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一论断表明:国家的理性建构成型,也即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呱呱坠地。这一决断既昭示了立法机关彪炳史册的功勋,也宣布了立法机关在法治舞台中心的退场。套用马克思那句话:立法机关努力完备法律的时候,也准备好了自己的掘墓人——法官。这是立法者的黄昏,却是夕阳无限好的黄昏!一个幽灵在法治舞台上徘徊,这就是法律解释的幽灵!其实,法律体系是否形成,可以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端赖主权者的决断。这就正如,一个孩子是否长得漂亮,大家心里都有自己的判断,漂亮与否,纯粹是个偏好,没有唯一正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可以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的研究,可以称之为“体系前研究”,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以前的研究。而之后,就进入了“体系后研究”时代。
体系前研究以服务法律生产为使命,各路人马都可以在法律产品的蓝图中表达“一己之私”,或者“爱恨情仇”,只有大开大合的激情奔放,无需丝丝入扣的概念计算。法学家可以是诗人,诗人亦可为法学家。体系后研究以服务法律适用为圭臬,技术正在替换思想,“大江东去”正幻化为“小桥流水”。诗性淡出,逻各斯之神显灵;偏好搁置,理性张扬。
体系前的时代可以称之为立法的时代,体系后的时代可以称之为解释的时代。
二
法律就从立法者的法变为法官的法,这是一个转身,却是一个华丽的转身!谁来解释法律?谁来传播法律的福音?当然是法官!文本一旦游离作者,又会获得涅槃式的再生,法律从立法者的怀抱走出后,就宿命地要变为法官的子嗣。
法律解释的时代已经来临,反解释的阴魂却舍不得退场,反而通过画皮来迷倒芸芸众生。还有理有据地抬出那个据说常人晚上不睡觉也写不出那么多文章的波斯纳,此君曾“打着红旗骂红旗”地说:法条主义正在遭受“实用主义、政治科学家、法律经济学家以及其他怀疑论者的摧残”,“法条主义的王国已经衰落、苍老,它主要限于常规案件,如今允许法官做的事很多。”法官要干什么?为什么还要抱着冰冷的法条哭泣?可以跃出自己的专业槽跑位吗?
在美国,离开法条主义的所谓司法能动是否真的构成对法律解释的颠覆?连波斯纳也不得不承认,常规案件的解决依然仰赖于法条主义。即便是非常规案件,法官在形式上也不得不从法条出发。在判决书上,波斯纳法官从来不敢露出一丝对法条的不敬。只有离了判决书,才敢如此汪洋恣肆。而且,美国法上的司法能动恰恰从司法对民主的有限干预开始,所谓司法审查中的“反多数”决,其实是解释对政治冲动的反制。越要能动司法,反而越要法律解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博克法官当年写过一本《美国的诱惑》,其中提到“法律的政治诱惑”。大意是: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极易受到政治的诱惑,从而放弃法律文本。法官遭受法律的政治诱惑又如何?也许我们会问。博克法官几乎用危言耸听的口气说道:法治“实际上在自由落体地坠入万丈深渊。”啧啧,联邦最高法院可能有人受到法律的政治诱惑,但这些人从来就不敢公开宣称:“我们依据的是政治,而不是宪法。”无论他们多么想“把宪法踢出法院”,也只能有“偷腥”的小动作,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宪法或者文本豪气冲天地扔在地上,再啐上一口。
离开法律解释,完备的法律体系一定是离地的安泰,万钧神力只能泥牛入海。法官也只有从法条出发,司法才不至于演变成另一场景的政治妥协。即便想加入一点道德考量之类的私货,也只能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在法律解释赋予的含义射程内调适。正是法律解释在法律与变幻不定的社会现实之间搭起一座不离不弃的浮桥,一方面使法律与外部社会保持动态适应,另一方面也使社会不再堕落为暴力和恣意横行的丛林时代。
“分析法学扮演的是仆人的事业”。以解释为使命的法律人,谦卑地俯身为法律文本的仆从——法律文本是其唯一的律令,以工匠自慰——通过对律令的解释求得纠纷的圆融。没有异想天开,没有灵机一动,更没有撒豆成兵,只有长期累积的解释技艺,只有训练而得的步步为营。工匠显得过于平实,没有金光四射,没有粉丝成群。《论语•问政》:“君子不器”,我们都想成为民族的“脊梁”,对技巧之类的玩意颇不以为然。只是,“脊梁”太多,就分不清真假,还容易闹出些“脊椎侧弯”或“骨质增生”的不治之症。
三
立法终有止息,解释不绝如缕。解释是戴着镣铐跳舞的事业,“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是舞者的基本功。解释者在解释的过程中,抱有对思想的高度怵惕。即便偶有所思,也低调地裹上规范的外衣。其唯唯诺诺之态,时常被斥“犬儒”。正处青春韶华的法学,本应挥斥方遒,奈何如此老成?“这个世界没有真理,只有解释”。自诩为太阳的尼采如是说。
世上最有价值的物什,一定是思想。不管今日哲人如何张狂,怎也走不出那个在小镇上散步60年的康德划定的世界;动辄将那个当年绝对称不上口如悬河的黑格尔从墓穴中挖出来祭旗,说明直至今日,我们也没有摆脱先人的魂魄。就是这些人,在不经意间划定了人类思考的一般秩序:没有硝烟,没有强力,却上演了实实在在的征服。
世界上最琐屑的物什,还是思想。甚至有人说,这是人和动物的区别。如果我们追问,世界上什么人思想最多?他们寄居何处?答案非常简单,精神病人,精神病院。他们每一秒钟都在产出不同的思想,迸发迥异的念头,只有精神病院才能安放如此之多的产出。
最有价值的思想,一定少而又少:思想史上的伟人凤毛麟角,这些伟人的思想体系始终如一。当下的中国法学界,有可以和伟人对话的强者吗?选择思想而不是解释的技术,我们进不了普林斯顿研究院,那就只能滑向思想的另一端:精神病院。芸芸众生,其实只有两个选项:精神病人或者俗人。一个世界,如果新思想叠出,思想家泉涌,那一定是不是文明,而是疯癫。
我们不满于规范构造的编码世界,汲汲渴求于法律背后的道德,以为自己从此不再肤浅。通过价值探求能否发现人类生活的真义姑且不论,但那些自诩发现终极真理的人却给人类带来过深重的罪孽。如果没有法律达成的舞台,所谓的诸神之争,只能演变为“群魔乱舞”,情绪的洪流最终会吞噬人类生活的“稳态结构”。法律解释将自己禁锢于规范的牢笼,通过小心翼翼的探雷扩大人类生活的意义世界,少了份振臂一呼的惊天动地,多了份解释的戒慎恐惧——这是平平淡淡与从从容容的真生活。
轰轰烈烈历来就属于立志改造历史甚至创造历史的风流,平民只求在“平安是福”中终老。以革命为圭臬的法律是帝王将相的法律,以解释为使命的法律才是平民的法律。只可惜,帝王将相从来就无须法律,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法律。
四
离开解释的立场,我们会掉进一个自己给自己设计的陷阱:近乎偏执地批评法律。而且,我们相信这种批评一定是有道理的:因为法律不完善,甚至有可能,法治就是帝国主义颜色革命的一部分。其实,我们说法律不完善,逻辑大有问题;说法治是帝国主义颜色革命的一部分,更显荒唐。说法律不完善,大体上有这样几个标准。第一,法律没有满足我们的某种道德理想;第二,我们的法律没有和国际接轨;第三,法律不能解决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因此存在空白;第四,法律没有回应民众的诉求。
法律没有满足某种道德理想是法律的缺陷吗?法律和道德的分离恰恰是法治的前提,否则我们会重蹈“德化”的覆辙。即便高谈法律道德性的富勒,也低调地认为:法律包含了作为义务的道德,作为愿望的道德,最多是法律的理想。我们让法律承载我们全部的道德理想,让法律负载其生命中不堪承受之重,无异于将法律“宗教”化:只有上帝全知全能,法律不是上帝。
法律没有和国际接轨不一定就是法律的缺陷。什么是国际惯例,这就很让人纠结:有说服力的定量分析如凤毛麟角,一句“西方发达国家如何如何”,“世界上多数国家如何如何”,雷霆之势骇然,但其中的技术含量,比阿Q叫人革命高明不了多少。再者,即便国际惯例是那样,法律作为地方性知识,并非全部都要和国际接轨:西餐的烹调方法不能作为否定中餐烹调方法的理由。
法律的确可能解决我们生活中的所有问题,法律决不是万能的。当然,现行法律比那些批评法律的人想象的要健硕得多,说法律不能解决眼前的问题,可能仅仅是因为我们缺少解释法律的耐心:从一般性规范到具体的个案,需要平心静气地解释。法律不是装在锦囊里的妙计,一遇困阻,便打开锦囊,于是柳暗花明。拿破仑领衔起草了法国民法典,梦想绕过法律解释的技术屏障,自认法典优美完备,可以让从未研习法律的人也能从中找到解决纠纷的答案。但在民法典的第一批评论公布以后,拿破仑怅然若失:“我的民法典已经逝去”。其实,拿破仑的民法典没有逝去,只是因解释而重生。
法律不能简单地随民众的诉求而摇摆,在民主的立法程序中,人民的意志已得到最大化表达。人民的意志已经通过立法程序释放,批评法律的声音不可能是真正的民意,民意可能仅仅是个“幌子”。
只有法律解释能力孱弱之时,才会批评法律不完善,亦如武功低劣者,才会批评武器。武功臻于化境者,对武器的要求几乎降为零:一根鸡毛掸子,在叶问大师的手中,也可以化作御敌的利刃;大理段家的“六脉神剑”,其实根本就不用剑。只有那些初入武行者,才会梦想“倚天屠龙”,想以此独步武林,最终引来杀身之祸。在法律人看来,法律因解释而完美,因解释而生动。女人都是美丽的,女人的丑陋一定是化妆师的败笔;同样,法律都是完善的,法律不完善是法律解释者的失职。
对于部门法的评判只有一个标准——是否合宪,对于一部合宪的法律,我们应该强行终止价值追问——不管这种追问来自伦理学还是社会学。立法是一个大众选择的过程,而这个选择只要在宪法设定的价值底线内,符合宪法规定的程序,就超越对错。对于宪法,只要没有逾越人类生活的基本伦理,就是正当的。接下来的事情,于法律人而言,仅仅是解释。
中国法治是后发型的法治,诸多概念和体系从西方移植而来,让国人生出许多隔膜。解释的前提是认同,在没有基本认同的语境中,只有众声喧哗的批判,生不出温文尔雅的解释。
法律是不是资本主义的阴谋?是不是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是不是和平演变的一部分?如果这样,我们就“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了。我们把“中国国情”当成打倒一切的“葵花宝典”,移植的概念和体系,转口而来的法律方法,肯定会画虎类犬、雅乐走调,没准暗藏了资本主义的病毒,我们只能批判,不能解释。
问题的答案其实简单之极。耍阴谋的应该是聪明人,怎么会傻到给我们输入法律,让我们幸福?再说,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革命先辈成果的记载,革命先辈与帝国主义叫了一辈子板,怎么会接受“糖衣炮弹”?帝国主义如果连这点都想不到,早就被无产阶级解放了,省得耽误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工夫。法律是我们的法律,法治是我们的选择,法治中国更是我们自己的事业,与敌人没有关系。无产阶级也有洞穿帝国主义一切阴谋的慧眼,还有吃了“糖衣”,“将炮弹打回去”的谋略,犯不着诚惶诚恐地“因噎废食”。
五
法律解释秉持了人类最谦卑的生活智慧,饱含了对未出场的人民的敬畏。解释蕴含了这样的信仰:解释者不比立法者更聪明,解释者不比人民更高尚。解释者不生造“构造某法体系”的神话,也不发出“某法之反思与重构”的呓语。由“法匠”而法学家,这是解释者要走的路。经由“法匠”的训练,在崎岖的解释之路上跋涉,最终达致法学家的峰巅,是这个“速成”时代不堪忍耐的人生苦旅。法律需要解释,甚至法学可以化约为法教义学。至今,我们在法教义学的初阶上蹒跚:法律解释之路不是一步一叩的朝圣之旅,而是需用汗水和智识铺就的救赎之道。用不着嘲弄中国法学的幼稚,正因了这种幼稚,法律才与芸芸众生的洒扫应对相关。法律的价值蕴藏在规范中,经由解释的管道,汩汩而出,泽被苍生。没有解释,法律要么沦为国王卧榻之侧的屠刀,要么只是供人顶礼膜拜的圣物。
善男信女不喜欢“法匠”,崇拜“大师”。只是那些自称“大师”的,往往是骗子;自谦“法匠”的,也许是高人。大师固然令人神往。那恢弘的气度,充满磁性的声调,飘在云端的思绪,都象极了跨越千年的神马。只是,做梦并非人生常态,最终,神马都是浮云。我们要面对的依然是我们也许不喜欢,但却必须用以解决问题的法律文本。大师伟大可能仅仅是因为我们短时间内无法验证其方案,或者验证其方案的成本极为高昂。正因为如此,大师可以层出不穷——钱学森和张悟本都可以是大师。只是,钱学森一直称“自己没有什么贡献,应用了别人的贡献而已”;张悟本开场就以“名人之后”自居,以“养生大师”自擂,镁光聚焦,众星捧月,绿豆验方包治百病。被后人称为政治哲学大师的洛克,生前对大师充满鄙夷:“在当代,知识的王国里并不缺少设计大师……有幸成为一个清扫道路的小工——清扫一些知识的道路上的垃圾——那也已经相当有抱负了。”
大师一定是知识的异数。作为知识的异数,要么是天才,要么是蒙昧。因蒙昧成大师,靠的是“熊胆”;因天才而成大师,持的是天赋。“你无法通过传授而成为一位大师。要想成为大师,则只能依靠其与生俱来的天赋”,探求法律之路的霍尔姆斯大法官如是慨叹。
游离法律解释来使法学变得深刻,那一定不是“肖申克救赎”,反而可能上演“人治”的“无间道”。以自己的偏好批判甚至替代立法者的决断,背后蕴含着知识人“致命的自负”:我们比立法者聪明,我们比人民高尚。聪明与否、高尚与否本无唯一正解,但假设人类的贤愚智劣大体相当,却是最接近我们经验的命题。一部数易其稿的法律,在少不更事者看来,忽然变得千疮百孔,我们不禁要问:一个年轻的律师,一个涉世未深的学生,一个象牙塔中的学者,在10平方米的斗室,居然要一眼洞穿其中的玄机,该有何等法眼!灵机一动就设计出法律修改的方案,该是何等先知先觉!这样凌空蹈虚的结果,不是在给我们设计天堂之路,而是把我们导向地狱之门。以“批评法律”为由来显示自己的深刻,无疑自降法学研究水准:在非常感性的层面去表达我们对法律的理解,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外在的立场”。说法律应该如何,伦理学比我们更擅长;说法律实际上如何实施,社会学更精致。
以解释为使命的法律人,无法回避的宿命是:文本会修改,以此为根基构造的法学无法“永垂不朽”。但即便法学知识无法万岁,但终究能有有限的生命;游离文本的法学梦想流芳千古,但无法逃离早夭的“魔戒”:“价值之争”是政治而非法律,“法律之核”是规则而非写意。
六
法律解释标志了“法律是我们的法律”之在场感。法律不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绳索,是我们念兹在兹的生活方式本身。最近看到“水尽鱼飞”的说法,请注意是“水尽鱼飞”,而不是“水尽鹅飞”,颇为震撼。“水尽鱼飞”说的是生死相依,“水尽鹅飞”说的是移情别恋。用于表述法学研究的进路与困境,“水尽鱼飞”的说法更为贴切。
法律博客上有位博主名为“红尘的鱼”,很是传神。如果将法律人比喻为鱼,法律就是水了。法律人天天抱着完美主义的心态,叫嚣“水太脏了”,“水里的氧气含量太低”,“应该将水排干,再输新水”,梦想着上苍“普降甘霖”,这是“鹅”的姿态,与鱼的身份相去甚远。可以设想,如果将水全部排干,等着“问泉哪得清如许”,鱼等得起吗?世上本无“六眼飞鱼”,多的是“流言蜚语”,“鱼飞”的结局只有“鱼干”。 鱼只有爱水,才能救赎自己——这是鱼的宿命。
法律人一定不想做沙漠中的鱼,靠着自己的眼泪苟延残喘。因此,要避免“水尽鱼飞”的窘局,法律人只能爱法律,然后解释规则中的律令。这既是态度,也是生计。
什么是法律人可能的贡献?我们凭什么让一个贫弱的社会供养?法律人总逃不出这样的追问。解释,只有解释。在漫长的解释之旅里,表达法律人对法治的忠贞,对人民的忠诚,对权利的敬重,对秩序的敬畏。经由解释,回答“中国法学将向何处去”,也许,这就是中国法学的理想图景。

-
2014
05-05
-
2014
04-30
-
2014
04-29